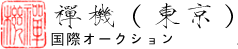解讀李可染的山水作品與市場行情
摘要: 山水畫《萬山紅遍》李可染作對於每一個熱愛藝術的人來說,李可染這個名字並不陌生,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在江蘇省徐州一個平民之家出生,排行第二,原名永順。“可染”來自他的小學圖畫老師王琴舫,王老師見他聰慧好學,贊曰:“孺子可教,素質可染。”遂給他…

山水畫《萬山紅遍》 李可染作
對於每一個熱愛藝術的人來說,李可染這個名字並不陌生, 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在江蘇省徐州一個平民之家出生,排行第二,原名永順。“可染”來自他的小學圖畫老師王琴舫,王老師見他聰慧好學,贊曰:“孺子可教,素質可染。”遂給他取學名可染。
8月,“可貴者膽—李可染畫院首屆院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這是對李可染畫院成立一年以來的總結。本次展覽共展出了140余位元藝術家的200幅作品,佔據中國美術館6個展廳,此次展覽除了展出了60余幅經過精心挑選的李可染先生的代表作品外,還展出了李可染師友的國畫作品,堪稱是一次現當代藝術家集體向李可染致敬的展覽。
對於每一個熱愛藝術的人來說,李可染這個名字並不陌生, 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在江蘇省徐州一個平民之家出生,排行第二,原名永順。“可染”來自他的小學圖畫老師王琴舫,王老師見他聰慧好學,贊曰:“孺子可教,素質可染。”遂給他取學名可染。
童年的李可染酷愛戲曲繪畫,常用碎碗片在地上畫戲曲人物,博得鄰人圍觀。13歲時的暑假,李可染在玩時見到當時集益書畫社的數位老畫師正在作畫,當下被迷住,伏在窗外觀看。從此一連數日,天不亮就在窗外候著,戀戀不捨。由此,拜徐州畫家錢食芝為師,正式啟蒙書畫,習王石穀一派山水。
1923年,李可染進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普通師範科,學習圖畫、手工兩年。這期間的收穫之一便是見到許多吳昌碩真跡。六年後,李可染考上西湖國立藝術院研究部研究生,師從林風眠和法籍油畫家克羅多(Andre Claouodot),專攻素描和油畫,同時自修國畫,研習美術史論。同年,杭州"一八藝社"成立,李可染為最早成員之一。
到了1950年代年代,國畫界變革的呼聲日高,提倡新國畫。李可染屢下江南,探索“光”與“墨”的變幻,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可以以“黑”、“滿”、“崛”、“澀”來概括其藝術內涵,為水墨世界開創出新的格局。而對李可染的藝術生涯起到關鍵影響的,則是他的一次長途寫生。這次寫生,歷時8個月,春季由北京出發,冬季始歸。所到之處,他觀察探索自然景物風雨陰晴朝夕變幻之奇,完成了數百幅山水寫生畫稿。此後,他的山水畫以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清新的筆墨意境獨樹一幟,在國內外發生了重大影響。
李可染山水畫早年取法八大,筆致簡率酣暢,後從齊白石習畫,用筆趨於凝練。又從黃賓虹處學得積墨法,並在寫生中參悟林風眠風景畫前亮後暗的陰影處理方式。畫風趨於謹嚴,筆墨趨於沉厚,至晚年用筆趨於老辣。亦善畫牛,筆墨頗有拙趣;將西洋近代繪畫注重感性真實和物件個性的特色融入中國畫的筆墨形式之中,破除了傳統山水畫輾轉相承的老程式,給作品注入了新鮮的生命感受和現代特色,是對傳統山水畫的突破,並由此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貌。
李可染的山水畫重視意象的凝聚。他強調作山水畫要從無到有,從有到無,即從單純到豐富,再由豐富歸之於單純。他在20世紀40年代的山水作品還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簡淡,是一種線性筆墨結構。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作品,借助於寫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線性筆墨結構變為團塊性筆墨結構,以墨為主,整體單純而內中豐富,濃重渾厚,深邃茂密。他從範寬、李唐、龔賢、黃賓虹等古今大師那裡汲取了朴茂深雄風格的營養,又迥然異於他們。他多取材于江南與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鑄了他風格中的幽與秀。他的純樸、醇厚的北方素質又使他的風格溶入了樸茂深沉。他又將光引入畫面,尤其善於表現山林晨夕間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種朦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從總體看,李可染的山水畫比明清山水畫更靠近了物件的感性真實,從某種意義上看減弱了意與形式趣味的獨立性。這是對於明清以來山水畫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傾向的一種補正和突破,且與五·四運動以來注重寫實的文藝思潮相一致。
李可染對寫意人物畫曾下過很多功夫,下筆疾速,動態微妙,形象誇張但不醜化,樸質卻不古拙,富於詼諧、機智特色和生活情趣,齊白石曾給予很高的評價。李可染還是畫牛高手。他喜歡牛的強勁、勤勞和埋頭苦幹,畫室取名師牛堂。多年來畫了大量牧牛圖。李可染善書法,喜搜求書帖,尤愛北碑。他的書法,得益于黃道周,亦得益於他的繪畫修養。重結體的建築性與神韻,態靜而多姿致,剛勁、蒼秀又溫絢樸厚。他為許多著作題簽,佈局構圖必經營再三,落筆即極具妙趣。
李可染有扎實的素描功底,他的作品讓人感受到了屹立千年的中國山水。一種範寬式的飽滿構圖,山勢迎面而來,瀑布濃縮為一條白色的裂隙,用沉澀的筆調一寸一寸地刻畫出來,綿綿密密地深入到畫面的每一個角落,在一張紙上,表現出最大最豐富的內容。李可染的水墨畫一掃逸筆優雅的文人積習,尤其是那以悲沉的黑色形成的基本色調,深深地抓住了人們的視覺。而在這悲愴旋律的制約下,畫中即使偶有淡淡的幽雅,也會被這“黑色世界”造成的淒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