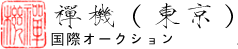新闻 > 收藏新聞 >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農民圖像與中國象徵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農民圖像與中國象徵
摘要: 符羅飛的素描《農民》 趙望雲1933年的冀南農村寫生《清河農人播種棉花》龐薰琹水彩作品《地之子》 符羅飛的素描《恨》 在1930年代國畫界中較為深入和系統地直接描繪農村狀況和農民疾苦的畫家中,趙望雲描繪的農村很全面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生活的狀況,採用高度寫實的水墨速寫技法更帶有客觀記錄的性質…

符羅飛的素描《農民》

趙望雲1933年的冀南農村寫生《清河農人播種棉花》

龐薰琹水彩作品《地之子》

符羅飛的素描《恨》
在1930年代國畫界中較為深入和系統地直接描繪農村狀況和農民疾苦的畫家中,趙望雲描繪的農村很全面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生活的狀況,採用高度寫實的水墨速寫技法更帶有客觀記錄的性質;符羅飛作品的思想和感情的深度遠遠超出了人物速寫這種繪畫類別通常所能承載的程度;而龐薰琹則在塑造中國農民的審美形象中,鮮明地引入西方宗教的圖式語言。
在1930年代國畫界中較為深入和系統地直接描繪農村狀況和農民疾苦,並產生較大社會反響的是趙望雲(1906-1977年)。他于1932年回河北家鄉農村寫生,並在天津展出這批農村寫生畫;1933年應天津《大公報》聘請赴冀南農村寫生,在報上連載130幅作品(後輯印為《趙望雲農村寫生集》);1934年繼續赴塞上和江西農村寫生;1935-1936年赴魯南水災區描繪災民生活;1948年隨軍隊赴湘黔苗區寫生。(參見《趙望雲年表》,載程征編《從學徒到大師—— 畫家趙望雲》,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7月)他描繪的農村題材極為豐富,很全面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生活的狀況;而他採用的高度寫實的水墨速寫技法更帶有客觀記錄的性質,完全符合報紙為他開闢的“寫真通信”專欄的題旨。
實際上,在趙望雲的這批冀南農村寫生作品中,直接描繪田間勞動情景並不是很多,而對於農村生活中的各種手工業者、集市買賣、家庭生活、節令風俗等情景多有描繪。趙望雲說,“我畫農村是由於我生在農村,熱愛農村景物,同情勞動生活”;(《趙望雲自述》。見同上書第15頁)“我是鄉間人,畫自己身歷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種生活上的責任,此後我要以這種神聖的責任,作為終生生命之寄託……我以為這十余縣的平民生活,至少可以代表華北農村生活之一部,如此樸實勞苦的平民生活,現下已逐漸趨向不安與動搖。”(《趙望雲農村寫生集》自序,見同上書第25~26頁)這是一種自覺的使命感,是在政黨革命思想和左翼思潮的籠罩之外根據自身生命的經歷、體驗而生髮出來的農村關懷,在中國現代美術的農村題材和農民圖像藝術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意義。早在1928年,王森然就說趙望雲在藝術圈中有中國的米勒之稱;在1930年代初就認識趙望雲的葉淺予在晚年回憶說當年《大公報》范長江的“旅行通訊”和趙望雲的“農村寫生”是最吸引讀者的欄目,他認為在趙望雲的筆下出現的農民是苦難中國的象徵;關山月在回憶中也提到,當時有人譏諷趙望雲說“無非會畫農民”;黃蒙田也回憶說,當時國畫界絕少有人畫農民題材。(見同上書第19~44頁)這些評論都注意到趙望雲的農村寫生在美術史上的特殊意義,這種意義實際上與農民革命畫和左翼木刻運動中的農民題材所具有的意義是並不相同的。
同樣重要的是馮玉祥在看到發表在《大公報》的這些農村寫生之後專門為每一幅畫題寫的詩歌。(當《趙望雲農村寫生集》的第二版於1933年11月19日出版時便輯入了馮玉祥題畫詩130首)有學者認為這些詩歌大體上是三種模式:“以文配圖”、“由圖引申”和“望圖生義”,馮的動機是“宣說自己對農村問題的看法,包括缺乏工業化的基礎、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宰製以及官僚體系的腐敗無能,並且混容著感時憂國的情懷,將不得抗日的挫折感,轉譯成鄉土或將不保的警讖”。(曾藍瑩《圖像再現與歷史書寫:趙望雲連載於<大公報>的農村寫生通信》,載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12月) 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但還可以再做一些分析。例如,《地頭少憩之老年農人》的題詩是:“農人耕地,自食其力:出自己汗,吃自己飯。本不焦慮,亦不困難:誰知贓官,苛稅強捐,民不聊生,農村破產!”(見前程征編《從學徒到大師——畫家趙望雲》第62頁)明顯地把農村的自然經濟與超經濟剝奪的緊張衝突作為農村對立的二元模式揭示出來,與黃新波等人的左翼木刻畫所表述的苛捐問題是相同的。《清河農人播種棉花》的題詩是:“春天到了,人人都歡喜,只有農人又該忙著種田地:一個在前拉著驢,一個在後推著犁,還有一個拿著籃,跟在後邊撒種子。三個人,湊成一架笨機器,外國種地用機器,我們種地用氣力。”( 同上,第61頁)這裡表達的是對農業生產現代化的願望,帶有一種現代性的目光。
可以說,趙望雲的寫生圖像本身與馮玉祥的題詩在思想維度上存在著某種差異性,而馮的思想與圖像的關係似乎恰好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日後農民圖像往政治性和現代性兼而有之的發展方向,就像在大躍進時期的詩配畫一樣,只是敘事語言變了。
符羅飛(1897-1971年)來自貧民底層,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自覺地皈依共產主義信仰的美術工作者。他參加了“五卅”運動和1927年的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擔任過法租界的工運宣傳員。大革命失敗後他被迫逃亡,到義大利繼續學習美術。抗戰爆發後,他從義大利回國參加抗日鬥爭。在戰爭期間,符羅飛在桂林參加了抗日文化界的一些活動,宣傳抗日。1946年,他赴湖南災荒地區寫生,回來後在廣州、香港舉辦“饑餓的人民”畫展,受到文藝界的好評。
在這批作品中描繪災區農民的兩幅速寫肖像中,作者敏銳而準確地描繪了南方農民的形象特徵,同時更為深刻地表現了人物的內心感情,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突出了對眼睛的刻畫,這也是符羅飛此期人物速寫中常見的表現手法。他自己曾這樣描寫過那些眼睛:“這是一對饑餓的眼睛,一對智慧的眼睛;它充滿著忿恨,充滿著反抗。在騎樓底,在茅蓬下,到處都是默默的閃光。”(轉引自黃蒙田《符羅飛十年祭》,香港《文匯報》1981年1月10日)
在速寫肖像中,藝術家對農民的命運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同時也揭示了農民身上所蘊藏的力量,其思想和感情的深度遠遠超出了人物速寫這種繪畫類別通常所能承載的程度。
在1930年代中國藝術家筆下的農民圖像中,像龐薰琹(1906-1985年)的《地之子》這樣的作品是極為獨特的。該畫原作為油畫,此為水彩畫稿圖,但是卻已經比較完整地表達出作者的主題思想。畫家也是因當年江南大旱有感而作,但是在畫面上並沒有極力渲染災荒的情景,而是把筆觸引向了更深沉的思考與情感。作為深受西方現代藝術影響的現代派藝術團體“決瀾社”的組建者之一,龐薰琹在